核心提示:《遭遇警察》一书在港出版。”译者”在线采访了本书的共同编者华泽女士,书面采访了另一位编者徐友渔先生。话题围绕着”喝茶”展开。
中国21名维权人士和网友讲述遭警察非法拘禁和殴打的经历汇编成书,起名为《遭遇警察》。
这本书收录了多位中国大陆主张阳光政治、公民权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被”喝茶”、被绑架、被失踪、被”戴黑头套”、乃至被侮辱和被殴打的经历,他们包括维权律师滕彪、许志永,”天安门母亲”成员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还有刘沙沙、王莉蕻、冯正虎、古川、”福建三网友”等维权人士。
《遭遇警察》一书的主编是中国的知名独立学者徐友渔和旅美纪录片导演、作家华泽。他们认为,中国已成为警察国家,他们是用记录来表达反抗。以下就是译者访谈第8期《遭遇警察 谈谈喝茶》
文字版:
今天我们的访谈主题就是遭遇警察,谈谈喝茶。我们的嘉宾是 《遭遇警察》 一书的共同编者华泽。
YZ:我是叫你华泽还是叫你飘香?
华泽:都可以。
YZ:那还是叫你华泽吧,因为你们出的书的署名是华泽。
YZ:想先请你谈一谈编这本书的背景,我稍微知道一点,就是去年你也经历过被”黑头套”、被恐吓的过程。是不是这个过程触发了你想要编《遭遇警察》这本书?它讲的是中国公民在触及维稳体制时所发生的事。
华泽:这是原因之一。这本书是我和徐友渔老师两个人编的。我们两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这个经历是我们的动力之一。但直接触发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是去年网上发出匿名的茉莉花革命的帖子之后,国内有很多很多朋友被抓了、被失踪了、被酷刑了,有些人被判了刑。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在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接近200人。这么大规模的抓捕,我们认为是64之后最严酷的迫害。这个消息传来我们都非常震惊。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了,有一段时间我跟徐老师经常联系,我们觉得我们要做些什么,对这件事有所反应。虽然我们不能阻止他们继续迫害国内的异议人士,但是我们可以记录,所以当时我们就讨论说要编这本书。
YZ:在您的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异议者们经历了不同”级别”的对待,比大家预期的都更严重。像我们平时经常上网,或者上推特的网友最常见的是”喝茶”,还有的人在自我介绍中会写道”喝茶认证”,那么我想知道,就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如果遭遇警察的话,会有哪几种不同的严重程度?
华泽: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我们也谈到,我们不是想在这本书中来力求揭露这件事的残酷性,这种残酷性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身上都发生过了,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遭遇警察更多的表现在于无处不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注意挑选的是不同的人群,比如有大学老师、维权律师、工程师、学者、纪录片导演,包括我们不认识的网友的文章,是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他们经历的遭遇也是不同层次的。有的是”喝茶”,就是”非法传唤”,有的是被”黑头套”绑架,有的人是被失踪,有些是被判刑,很不一样。我们选择的时候是有这种设计,让它反映出各种不同的遭遇,因为篇幅有限,在25万字的篇幅里,我们要体现出一些样本意义。
YZ:你刚才提到无处不在,这和我们平时的感觉一致。如果有一个敏感词列表,就是如果你写了关于这些的文章,那么帖子会被删掉、你也会被”喝茶”,那么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预期,知道红线在哪里,但是我们之所以觉得它无所不在,就是因为没有这条红线,或者是”隐形的红线”,全部都要凭你自己去判断。那么,比如我们会认为,翻译不会踩红线,因为我们是在引述别人的观点,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它让你感觉的这些想法都不是他明文说出来的,那么当你真正遭遇警察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做什么怎么也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共有的经历,完全没有预期,也没有规则可言。
华泽:在一个”法律不是挡箭牌”的国家,谈预期是完全不靠谱的事情,有人说我会做事,我永远都知道边界在哪里,我会做得更长久一些,我不会让自己突破那条红线。我不相信这种话,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为自己作辩护,事实上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有什么都不做才可能安全。只要你做一点点,你很可能就会遭遇警察,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边界在哪里。
YZ:是的,这我也深有同感。就是你自以为在安全区域,实际上都是自我安慰。从去年开始出现的很明显的人权状况的倒退,也就说明了没有这种安全区。如果你还骗自己说只要我不做什么我就还安全的话,那么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华泽:在中国你什么都不做,有可能是安全的。但这句话也不确定。比如很多很多访民,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可是有一天突然大祸临头,他们就被逼成了访民。
YZ:虽然这本书在国内被禁,但大家还是可以去找来看一看,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会是重要的心理建设,我就想到了XXX的例子,她是一个90后的小孩,她家被强拆,她爸被打成重伤,后来就死了,如果你去看她发的微博,整个变化就在一天之间,判若两人,前面还是大头贴、吃饭逛街、后面立刻就变成一个访民喊冤的微博了。控诉,寻求支持、怎么办?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应该破除一个幻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个小女孩。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的生活完全改变,会进入到更加真实的现实中。但这并不是你自找的,是你主动想去踩一条什么红线,很有可能是突如其来降临的。
华泽:在这个社会,只要你真实地生活,这个危险永远存在。即使你只想把头埋到沙子里,象鸵鸟一样,也有一天你可能会踩到红线。比如你看薄熙来,有一天他突然自己也变成了维稳对象,你完全不知道他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不管多高的官,总有一天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如此,比如当年的刘少奇、贺龙这些人,都是地位显赫的人,他们有一天也会死得那么惨。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
YZ:那我们转到下一个问题,假设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突然有一天遭遇警察,那么最常见的情况下,你知道他/她会经历一个什么过程?
华泽:这可能是因人而异的。我讲讲我自己”喝茶”的经历吧。那大概是2010年的3月份,那时我在网上发表了一、两篇和政治有点关系的文章。原来我做纪录片,和历史、文化有关,和政治关系不大。在我做”百年电影史”的时候,接触了一些老电影人,20、30年代就是地下党、左翼作家,49年后他们地位很高,但很快,有的从反右开始,有的从文革开始,从家里被带走,然后十几年没有消息,十几年之后回来的就是一个骨灰盒。但总的来说,我的工作是做历史文化的纪录片,和现实的关系不太紧密。201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寻找中国之路》,这篇文章现在想想挺空泛的,就是说中国那么多的问题,汶川地震、被三聚氰胺毒害的孩子,我认为大家应该讨论一下我们要怎么办,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就这么一篇文章就被他们找去喝茶了。
当时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有一天早上六点多钟,家里的电话忽然响了,我接起来,没有人说话。因为只有很少的亲戚朋友知道我家里的电话,我又长期失眠,睡觉我会把手机关掉,所以知道我那个电话的人都明白不会凌晨打电话找我。所以我就有些预感,当时心里还是很紧张。
我就打开电脑,把消息发到推特上了。电话再响的时候,有人就问我”你是不是华泽?”,我说”是。”他说:”我是片警XXX,你开一下门。”我把铁门上的小窗户打开,就看到门口有六、七个穿黑衣的大汉。其实,对待我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感觉就是他们想恐吓你。否则的话你说我一个小女子,有什么必要来六、七个人?
我当时穿著睡衣,他们站在门口说:”你穿上衣服,和我们走一趟。”我显得很镇静,但心里感觉在狂跳。然后我就换了衣服,跟他们出去了。他们把我带上一辆黑车,开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那次”喝茶”整个过程也挺客气的。
一进去他们就说: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们说,你跟警察打过交道吗?我说当然打过,我拍片子,拍过警察。他们说,你把手机关掉。又说:你有没有带录音设备?我说没有,他们就说,那我们就不搜你身了。当时基本上还是很紧张,他们说什么我就答什么。
YZ:都是守法公民啊。我知道的很多”喝茶”的情况下,被喝的人都是非常顺从的,很多都是经过了之后才想起来,然后骂自己:我怎么这么傻?一点儿反抗意识都没有?怎么连出示证件给我看我都没说。
华泽:我倒是说了,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出示证件?他们说:有必要的时候会给你出示。因为整个过程都比较平和,他们也没有恐吓我,就是说想找你来了解一下情况,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就问他们:我这篇文章违法吗?他们说我们不就这篇文章的性质来讨论,我们只是想知道你写作的过程。我就大概说了一下,是我写的,为什么写。然后他们又问了一些问题,比如你都跟谁往来,有没有谁让你做这件事?历时3、4个小时。
YZ:很典型。我说典型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更多类似的情况。比如他们为什么会问你交往的人,他们的关注点为什么不在文章本身,而是在它出台的过程。因为他们真正的敏感点是说你是不是想组织什么事。
华泽:对。
YZ:他们所有想挖出来的线索都是围绕着,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组织,是不是有人让你干什么,然后你再去呼吁、发展你下面的人。他们就是这样的思路,他们所做的都是要套这些信息。一般的人,比如说你因为某篇文章而”喝茶”了,你会去讲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我的观点是怎样怎样,但他们并不关心你的观点,他们关心的是你是不是想组织闹个什么事。
华泽:第一次”喝茶”让我震惊的是背后的东西,我仅仅是写了一、两篇文章,在那之前我都不怎么上网,我也没有什么网友,他们居然追踪到我,而且把我发在网上的文章都作了详细的调查,还有我的身份,他们都作了调查。我就觉得特别震惊,我这么一个人值得他们这么做嘛?
YZ:对,这个心情也很常见。因为一开始大家是匿名发帖,自我感觉是这是没人知道的,一般来讲要到”喝茶”那个点上,你才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叫“老大哥在看着你”,如果他们开始盯上你的话,到请你“喝茶”,可能中间有一、两个月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是纯透明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这就很有意思。其实你是生活在牢笼里,四周都是摄像头,但你自己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比如你开车在高速上,我知道前面有一个摄像头,我觉得还好一点,因为如果我超速的话,我明白会出现什么事。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状态下,就是你本身很透明,只有你自己以为你还有隐私,所以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
华泽:是,我的很多朋友,我们知道最轻的是“喝茶”,接下来如果升级,你就会被上岗,在所谓敏感的时期,他们会待在你家门口,你要出去,他们会跟着你。你可以出去,但要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再比较严重的就是软禁,不许出去,你被看在家里,但你还可以上网,可以跟朋友联系;再比较严重的就是你会被绑架,而且是被秘密绑架的状态,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去哪儿了,在里面他们会威胁恐吓你。这种威胁恐吓是非常切实的,像我和一些朋友被绑架的经历,你是被突然带走,带走你的车没有牌照,周围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用黑头套套住你?首先就是一种恐吓,因为戴黑头套是很恐怖的一件事,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他不想让你知道你去了哪儿,让你对周围的环境完全陌生,处于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经历了被恐吓的过程。比如告诉你说,你想坐牢,我们不会给你当英雄的机会。没有人知道你到这儿来,你可能一、两天就能出去,你也可能一、两个月才能出去,你也可能一、两年才能出去,你也可能永远从此消失。你在里面的感受是非常真切的,你知道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做到。
这种比把你判刑、坐牢还要恐怖。判刑坐牢有一个时间点,你会有一个期待,如果见到律师还可以公开说,别人可以对你进行声援。但这种非法拘押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当时我对自己行为的评估是离这个还太远了。我只是偶尔被”上岗”,还没有很严重地限制我的自由。然后突然一下就被黑头套绑架,所以你根本无法预期你是在这个、还是那个”被维稳”的阶段。从我自己来说,我也不觉得我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是我做了,我还觉得值得。后来也有一些网友质疑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遭遇?是啊,我也不知道。
YZ:好像你自己觉得我还没有到这个档次。
华泽:那次刘晓波获奖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被秘密绑架走,有人认为”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的发起人没有被绑架,我只是一个签署人。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发起人把”声明”交给我,第一批签署人是由我征集的,之后是我在管理这个签名邮箱,把我抓起来之后这件事就停止了。当时几天之内就有1000多人,抓了我,就没有人做这件事了。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之前我也有参与”三网友案”、”公盟”的一些活动,跟维权律师走得也比较近。他们会积累起来,我想如果我仅仅做这一件事可能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YZ:很难说,这个都很难说。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去猜测什么是它的触发点。更有意义的是告诉更多毫无心理准备的人,第一是你认为的安全是一个幻象,第二是你认为你的等级不会升级,这也是一个幻象,因为这些都是没有规则的。
华泽: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中,你对所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行动都没有预期。
YZ:是的。唯一还可以说的是,他们是按一个处理流程在做,不管是你也好、薄熙来也好、艾未未也好,可能大家在社会上是不同的状态,可能还会有一些社会地位的差别,但是你一旦进到那个机器,都是一样的,都是按同一个流程来做的。收手机、黑头套、绑架、恐吓的很多话都是一样的,最后让你签什么,这就是一个流程。假如有人知道这个流程,在黑头套套上来的第一分钟,大概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这很重要,这对他/她后面的判断会出现变化。如果这些你都是不知道的,要到发生到你身上,人家跟你说:”你这辈子见不到你妈了。”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他会怎么说,在那个环境下你突然听到这个话;和我们现在这样,相对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下来谈这个事,告诉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你可以假设一下,在这个状态下你会怎么反应,那如果真的面临这种状态的时候就会好一些。可能就没那么震惊,心里的起伏波动也会少一点儿。
华泽:对我来说,第一次喝茶我挺震惊的,非常慌,后面就没有什么。
YZ:那你属于心理非常健康的。我觉得”喝茶”总会有一点让你”直见性命”,你平时不认为我是这么一种人啊,比如,我不会出卖朋友的,但是你是要自己经过了你才能给自己下这么一个评断。或者你平时可能会想:那个人对我不是很重要,但是当你被非法拘押,你突然很想见他。突然觉得原来这些人对我这么重要,其实这个事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一个反观。
华泽:因为我跟中国最敏感的那些人是朋友,所以很快我就知道了他们的种种遭遇,看了很多文章,听到了很多遭遇,所以我觉得我被绑架这件事是早晚要来的,只是没有想到来得会这么快。
YZ:哦,那你和很多人不同,不少人都没有这个准备。往往是在这个过程中才会显露出他最本来的那一面,没有经过思考就反应出来的那一面。
我还知道有一些朋友经过了这些事之后都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我知道一个人,我开始以为他是外国人,他长得样子像外国人,跟我说的也是英语。我们在国外谈起来的时候,不过是讲讲人生经历,我才知道他是一名维族人。我们说的也不是很敏感,他就突然说:”我们讲的这些他们都是知道的,他们的监控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早就被监听了。”其实那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是它留下的阴影是很大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你已经平静地生活了,但某一天那个念头就会闪现,根本就没有改变,我还是在那个小黑屋里,他们把我放出来是一个假象,让我出来钓鱼。会有这种情况,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心理幻想。
华泽:对我来说,我对所有的控制都非常敏感。从第一次找我”喝茶”,我就已经知道,因为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就知道我的电话被监听,我的电脑被监控,我的行动被监视,所以是有思想准备的。
而且我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我要让我的生活处于正常的状态,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要保持自己非常好的心态。我知道有很多人被放出来之后,依然处于恐惧之中,甚至他们怀疑周围的一切。
YZ:对,多少会有这种感觉。有的心理承受力差的,有一位大学生,也是因为一个很小的事,就”喝茶”,后来他的毕业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就不断地认为是别人一直在监控他,他之所以碰到这么多挫折,都是因为这个事根本没完,他还是处在被隐形监控状态,最后他怀疑他爸他妈,所有的人,真的成了心理疾病,后来是自杀还是自杀未遂。像你说的情况,你是怎么调节过来,告诉自己说,哪怕他们现在就在门口站着,但是我还是要过得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这个挺不容易的。
华泽:这个可能和每个人的个性和心理素质有关吧。我一直觉得,如果他们把你放出来了,但是你还是处于恐惧之中,他们就非常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是想让你们陷于恐惧之中,精神或者思想或者肉体被他们所控制。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即使我的肉体被他们控制,我的精神也要是自由的。如果我被放出来,我内心还一直处于恐惧中,我绝对不能这样。
我从小就对所有的精神控制极度敏感,我就是要摆脱、要反抗,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YZ:我希望如果有读者或听众存在这方面的恐惧的话,能对他们有帮助。我是经常碰到一些很小心的读者,他们专门设一个邮箱来接收我们的译文,这个邮箱只是收邮件,同时他还是担心这个行为已经被监控了,然后会有人把我抓走,就被73条了。
不过知道了这么多故事之后,我也觉得这种自我设限或恐惧是不是也有点过了。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讲?
华泽:我从来不做自我审查。包括我原来在体系内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片子每一期都要受各种各样的审查,但我自己绝对不做自我审查。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你们告诉我说:这个是不能做的。我会据理力争,但是我不坚持。因为我知道争下去也没有意义。但是我一定会去试图碰那个线,因为那个线是你不碰它,它永远在那儿。你要不断地碰它,它才变得有弹性。你要去碰它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突破。如果你不去碰它,你又自我设限,你的心就会越来越被包起来,而不是开放的。
YZ: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一些人,经历不同,感受不同,比如有的人在文革中自己没有被批斗,他只是看到别人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他的这个恐惧更大。那些亲身经历的人自己觉得,我应该去做,我不要给自己设限。但是别人看到了这个过程,他的设限的意识反而更深地嵌入到了脑子了:啊,千万不要轮到我。其实,这也是一种经历嘛,你经过了可能对自己还能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我有时有些担心,如果我们老是说被活埋、殴打,如何残暴,对某些人来说,他知道得越多,他的恐惧越深,他觉得第二天警车就会停在我楼下了。其实他的做的那个事离真正的喝茶还差得太远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害怕的话,先行者的意义反而没有了。他们那么勇敢地冲在前面,结果只是当了”杀鸡儆猴”的”鸡”的话,那实在太有违他们的本意了。
华泽:我认为”如果都……”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永远都有不同的人,不可能都如何如何。面对一件事的反应,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对有的人来说,这件事会让他变得更警惕、更自我设限、会缩得更紧。对有的人来说,反而会激发他反抗的力量。对我来说,如果一切都风平浪静、和风细雨,我也不会和别人发生冲突。但是如果有非常强的企图控制我的力量时,我会发生非常激烈的反抗。对我就是,你的压力越大,我反弹的力量也越大。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而言,精神上受控制比肉体上受折磨还要痛苦。
YZ:好,那么我们来谈下一个话题。在遭遇警察的时候,有些人会试图以人对人的方式来和维稳机器中的某些个体交流,比如聊聊”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看过多少人了?”我会以比较个人的角度,比较人性的角度来谈,你就算披着那身皮,你不是回家也有老婆孩子吗?你不是一样会有些担心,比如你家要被强拆了会怎么样?有时想想,如果我们和维稳机器碰到了,那么也就有了一个机会去了解,它是由哪些零件构成的。不过也有一些人说这种沟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象《窃听风暴》里的那个角色,他因为一直窃听”异议分子”的话,结果他自己转化了。你认为应该怎样看待维稳体系中的个人,是把他们当做机器中的零件呢,还是当成一个人?
华泽:我会把他们当成人。我一直相信每个阶层,每个职业中都由不同的人组成。国保队伍有几十万人了,它也是不同的人组成的,不会是铁板一块,我一直坚信这一点。当时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会让你从此消失。我很自信地告诉他们说:”我不相信。”我说从头到尾,从抓我、看我,到管我的人一共有30多个,我不相信这些人都是铁板一块,我坚信不疑。比如说你们真的把我活埋了,今天可能没有人说出去,你能保证10年以后、20年以后都没有人说出去吗?这个社会总是要变的。没有一个人有良知吗?我不相信。在我被关进去差不多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有8个人日夜看守,每天24小时换班,每天朝夕相处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我跟我妈有很多年都没有这么长时间住在一起了。怎么可能永远不谈呢?你也不可能总是一种对抗的状态。而这些人,他们来看守你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他对你也有一点好奇。比如说一开始他可能认为你是异议分子,是反党的,对国家安全有危害,可是当他接触了你,他会觉得你不是啊,你其实很平和。他也很好奇,试图跟你交流。这种交流总会存在。在这个过程上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会很同情你,打心眼里尊重你,但是这是她的工作之一,她没有办法。还有一些,她表面上对你也不错,但她会做出偷看我的笔记、把我的东西偷偷拿走去报告这种事,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在审讯的时候也有唱红脸的、唱白脸的。
YZ:我觉得我们的答案很相似,会想到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利用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审讯方式,目的是一样的,希望你能说出他们想要的信息。虽然你自己可能觉得,我根本没有这些信息,你们完全搞错了。但是它是这么设计的,这么安排的。不过我觉得也要增强一些自己的心理建设,不要完全不相信别人,觉得所有都是一种维稳机器的操控下的表演,因为那样就会陷到”喝茶”后遗症中最坏的一个结果,无法消除恐惧,然后你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牢笼,即使你走出了那个有形的牢笼,也无法走出你的的心魔。
华泽:对有些人,可能喝茶就那么两、三个小时,这以后可能就再也不会找他了。但他很长时间都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就是它们对你的控制虽然已经释放了,但是他们其实是在利用你自己对你进行控制。
YZ: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艾未未会老是去复述/还原他被非法拘押的过程。这是一个人走出他自己的牢笼的必然阶段。你要换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它也是很值得经历的。如果不经历的话,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你心里还有这样的一面,有如此胆怯和不敢正视的一面,当你经过之后,你反复去想,可能会了解的更多一些,甚至会完全改变。有的人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谨小慎微,还有的人都会变得无所畏惧。虽然你们可以施加的监控还可以升级,但是对我而言,我的心理恐惧一旦突破之后,不管你是蒙眼还是黑头套还是的殴打,那只是你的手段的变化,但对我而言,这个魔咒就消失了。
华泽:更多的时候,他们无论绑架也好、”喝茶”也好,其实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多。因为他们找你的时候他们对你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监控,实际上你在他们那儿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他们之所以恐吓你,要你说这个说那个,其实是对你的自尊的一种摧残。
YZ:其实就是一种对意志的消磨,就是改造思想嘛。
华泽:还有写保证书也是这样。
YZ:对,这个其实很可笑,就算写了又怎么样呢,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签了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这整个过程,比如你说你承诺再也不如何如何,它有一个心理作用,这在后面会有一种负罪感,好像我已经承诺过了,我违背了誓言,其实这些都是在打心理战。
华泽:很多人要对自己做一个心理评估,就是你自己能承受什么,如果你承担不了就不要去做。还有一些人,我称他们是”键盘革命家”。他们会在网络上以非常偏激的语言去发泄。但是在现实中,我知道一些人是非常胆怯的。现在你在网上发言也是会受到监控的,那么实际上你没有准备承担现实中的责任和义务,就不要去做这种网络上的勇士。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在做一些幕后的默默的工作,那些工作也非常有价值,有意义,不是每个人都要冲到最前面,那么就是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对自己说,我没事,不会怎样,其实不一定,你一定要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做一个评估,如果不能承担,我们知道,去年抓进去就有人出来得了精神病的,这样的话,就是你没有做好准备。
YZ: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谈话能帮助到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心里的魔障,每个人可以从今天开始就想一想,你自己的承受力有多大,你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非常谢谢你,华泽,我最后还要提一下,这本书的另一位共同编者是知名学者徐友渔先生,我们得到了对他对我们采访的书面答复,我会附在访谈的文字版的后面。
谢谢,再见。
———————
徐友渔老师回复译者访谈:
① 您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先谈谈签署之后您的经历吧。在经历了这些之后,您是否能够对《零八宪章》的意义做一个评价?
签署之后,单位的头头叫撤销签名,我当然拒绝。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期间,警察把我从家中带到昌平的某个地方看管起来。以后不断遭遇警察,比如不准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不许与外国作家谈话,不许应允给海外媒体写稿,甚至与国内朋友一起在饭馆吃饭也被骚扰。
《零八宪章》是中国人民追求一个良治、现代、文明社会的总的纲领,从文字上看,它只是重申了中国承认的联合国宪章、宣言,以及中国现行宪法基本规定的条文内容,但从它一诞生就遭到当权者打压来看,它确实表达了对于自由、民主中国的基本诉求。
② 我们知道您是知名学者,也是”八零年代”比较早把”自由主义”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学人,曾经是”文化热”中的重要一员。您这次以实名编写这本《遭遇警察》,想必也能料想到可能会出现的麻烦,跟我们说一说您为什么做了这样的决定吧。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亲身经历遭遇警察,他们把剥夺我的法定权利、干预我的正常生活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比如跑到家里来宣布这文章可以写,那文章不能写,又比如对我的某些出行、出访没有禁止,自夸为宽宏大量,以此要求我对他们”配合”,这激怒了我。他们把压制与剥夺视为正常状态,把偶尔的放行当成额外施恩,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还有没有宪法和法律?我决心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恢复本来的道理。我向警察宣布:他们的所作所为,促使我要写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是和谐社会,还是警察国家?”如果警察有记性,应该记得这句话,应该对出版《遭遇警察》一书不感到吃惊。
第二是2011年春季北非诸国发生”茉莉花革命”时,警察的疯狂镇压。许多朋友,特别是维权律师,遭到抓捕、虐待、拷打,令人极其悲愤。许多人只不过是顺手转发了一条信息、一个帖子,只是在饭局上随口议论了几句,就受到及其残忍的虐待。其实,就是按照现行的法律和警察以前一向的做法,也不该那样。事后的情况也证明,警察对于任何受害者都没有拿出证据,证明他们犯下了”危害国家安”或”颠覆政权”的罪行。自己感到末日来临,就把疑心的人定为预谋行刺者,哪有这个道理!在这”茉莉花恐怖”的日子里,我和华泽感到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既记载,又抗议那空前的倒行逆施。
③ 刚才谈到了”八零年代”,您在”阳光卫视”和崔卫平老师做谈话节目的时候曾经说过,您有信心,只要环境不是这么压抑的话,知识界有能力、有动力也有资源再推动起一场不亚于”八零年代”的”新文艺复兴”。什么让您如此自信,您不认为现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更多转向现实和物质的一面了吗?
我的专业性研究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我仔细、深入地研究过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的转型和进展,我本人也是其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认为,虽然有学风低下、腐败成风等严重问题,但进步和成就还是明显的。比如知识界思想的主流从专注于美学转变到对于政治学、法学的重视,对空泛的”蓝色文明”的礼赞转变为对于”宪政民主”的认同和追求,对于西方学理的简单介绍变为深入的研究,对于以前思想学术上的盲区、空白的重视和填补,等等。腐败、剽窃、滥竽充数是大面积的,但好在少数人达到的高度还是很说得过去。想想中国知识界在1989年学生运动涌现时的仓促上阵,到现在知识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何而来的反思有多彻底,对于思考中国未来的目标、方向、路径提供了什么样的学理支撑,就可以看出两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确实,现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更多转向现实和物质的一面了,但既然要谈不亚于”八零年代”的”新文艺复兴”,那就主要不是看侏儒有多少,而是看有没有巨人以及巨人有多高。而且,真正的、经得起历史潮流磨洗的思想文化成就,必须面对现代物质主义的盛行的。在贫瘠,缺乏水分和营养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当然,明显的不足是没有思想、学术、文化上公认的大家和代表性人物,这也跟当局的政策有关。但我看重的是,与80年代相比,现在的东西是实的,不是虚幻的。
④您是79年之后首批”睁眼看世界”的学者,不仅身体力行地引进国外的哲学流派,也很重视如何将中国介绍给世界,那么这本书《遭遇警察》您希望传递给世界什么信息?
在判断中国今日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政治弊端时,许多中国人、许多外国人都缺乏基本的价值立场,部分原因是基本信息的缺乏。我们出版《遭遇警察》一书,意在揭示真相,传递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不知道的信息。我们还想强调,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的存在和猖獗,是判断中国现状,是现在和将来评价执政党功过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任何人都不能装做没有发生的,是中国大陆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中国真正走向法治和现代文明时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当前的人权和法治问题,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2/07/8.html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2/07/8_05.html
 XU ZHIYONG, a lawyer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knew he risked his freedom by challeng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fulfill its vows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XU ZHIYONG, a lawyer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knew he risked his freedom by challeng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fulfill its vows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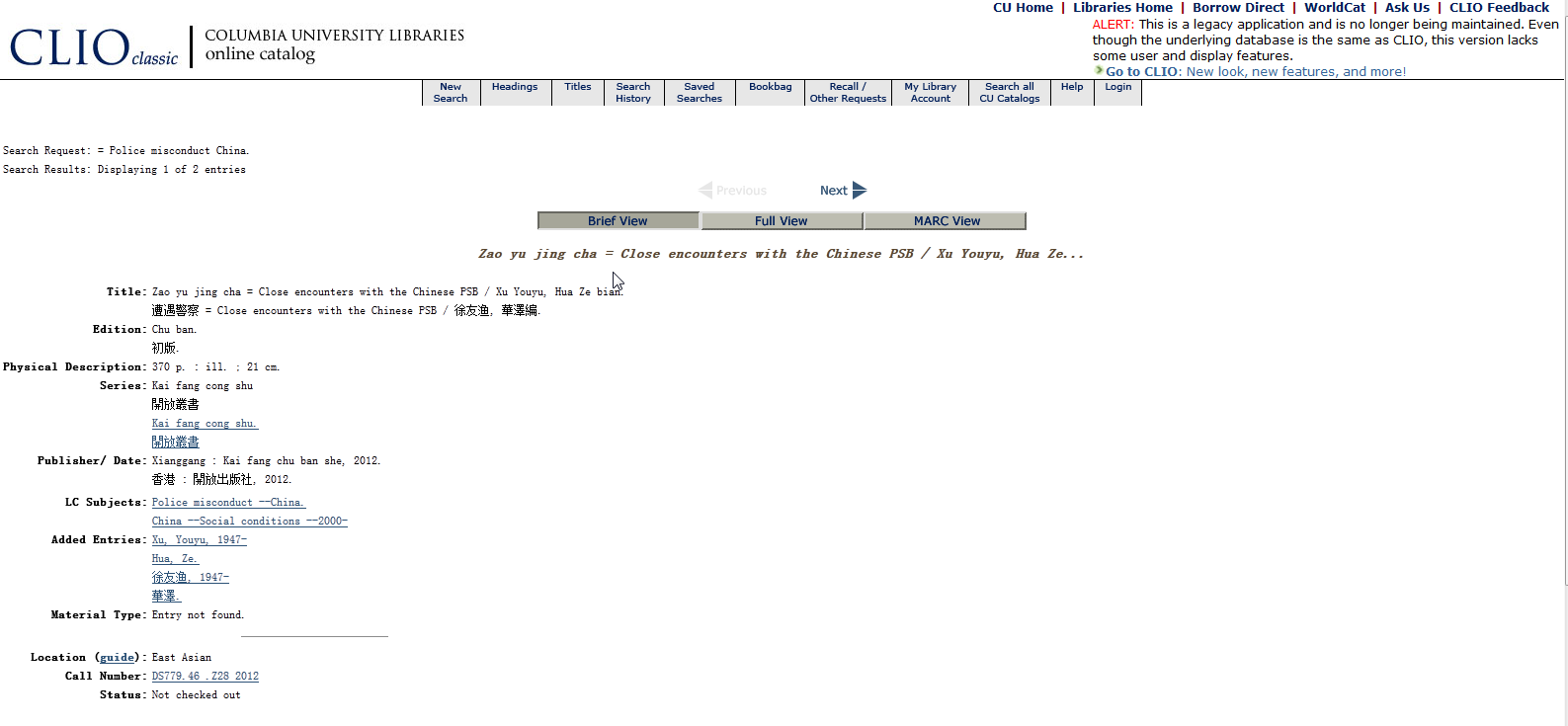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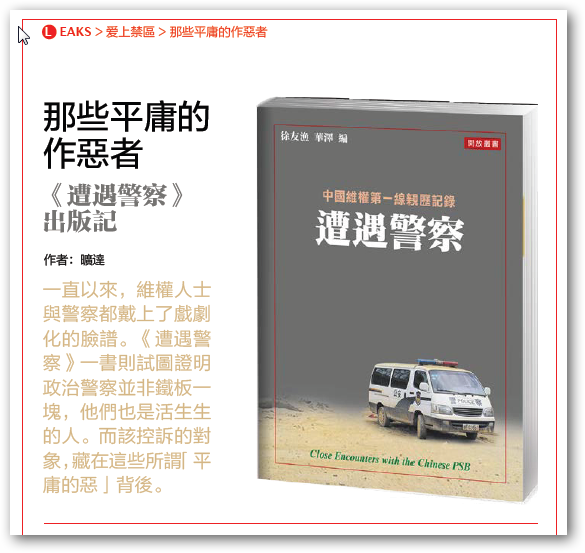

近期评论